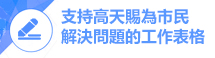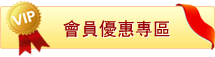本人記得在二零零六年三月舉行的會議曾發言,公開提醒現時很多前線且低薪的公務員在其工作單位受到迫害,隨後須到醫院的心理專科求診。
在接受本地傳媒訪問時,本人曾多次提醒上級對下屬的一些迫害和岐視方式可能引致一些可預見的悲慘結局。
二零零六年九月十八日一名統計暨普查局的編內女職員自殺身亡,留下一名幼兒由其配偶撫養,而其配偶也是該局員工。
我想提醒一下在幾個月前,更確切地,是在二零零六年七月十日,該女職員曾聯同另外三名員工舉行記者招待會,舉報在工作單位曾遭到人身脅迫及性騷擾,包括該局一些主管級人員有系統的勾結及迫害。
關於這些嚴重指控,可能由於沒有適當的跟進,公眾已開始淡忘,因而未被正視,直至到九月十八日才重新成為新聞焦點。
根據多個代表公務人員團體近幾年的統計資料,顯示患有抑鬱病和有自殺傾向的公職人員人數增加,大部份是與惡劣的工作環境有關的。
我們知道,在公共部門裏,當開始對員工作出迫害時,“羞辱者”、“攻擊者”、“騷擾者”通常會有預謀地把受害人孤立,令其承受心理壓力。自該刻起,由於恐防遭到報復,受害人的同事便不再與她談話。
這就是“受害人”在其工作單位開展她的黑暗生活的起始點。
紀律程式開始被濫用,因為不管事無大小都會提起有關程式,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在一個約五百名員工的公共部門,只在2005年就有五十個紀律程式。
受害人和證人表示受害人受到一些言語或動作或態度的騷擾,致令他們的人格、尊嚴或身心完整性受到傷害,他們的臨時性工作及負擔家庭生活的穩定財政收入受到威脅。
這些騷擾令受害人產生粗暴行為和出現惱怒、失眠、不安、食欲不振、思想反覆、沒法集中精神在工作和私人生活上,並與至親的家人關係惡化和加重抑鬱的情況。
騷擾者向受害人傳達一些令人混淆的指示,阻礙受害人的工作進度,誣衊受害人犯錯,在其他同事面前視之為透明、被要求趕交一些不重要的工作或制定一些不可能達到的目標。
超負荷的工作要求只旨在使受害人增加犯錯的可能性,以此達到可對受害人立即提起紀律程式,將數個處分相加來構成強而有力的理據對受害人作出更嚴曆的處罰和解除職務。
這些不可忽視的現實事件,在心理上,令員工的情緒結構產生極大的傷害。
我們在一些公共行政部門最常見的騷擾方式有:“騷擾者”與“受害人”拒絕直接對話,他們只透過第三者、字條或最郵方式聯繫。
有時,運用權力隔開員工的工作位置,即將“受害人”安排在一個孤獨的地方,那些寺方沒有工作工具和電話,但卻在嚴密的監視下工作,目的是讓“受害人”難以跟其他員工進行溝通和對外聯繫,而最主要是阻撓“受害人”發表意見。
我們還發現以下的情況:例如:不提升員工的職級、取消帶有特別酬勞的工作或撒銷定期委任和職位,幫意令“受害人”的財政收入受到損失。
許多時候借一些工作規定強加於某個員工,如果某個員工所做出來的工作與其他人不同的話,他就會處罰。例如:要求一名技術助理員擔任司機和郵差的工作,要他每天送文件,或在司機不情願的情況下,強迫他在星期六和星期日的假期裏去監督清潔其上司辦公室的工作,這影響了員工每週的休息也影響了員工的天倫之樂。
其他的專橫例子有:要求履行無法執行的工作和要求在極短的時間內完成工作。
常操控資訊,以免有關的資訊預先傳到受害者耳中,藉此孤立和削弱受害者在其同僚心目中的地位,從而成為同僚嘲笑和淩辱的對象。
還有一些荒謬的事,例如,若要去廁所均要請示,且限定次數。
總而言之,這種精神恐怖的管理情況發生在多個部門。這種充滿惡果的氛圍的出現,是因為主管是按親朋戚友的關係而被委任的情況有關。
雖明顯缺乏擔任領導主管職務的才能,但他們因受到上級關係的庇蔭而獲委任。為了彌補不足,他們會變成專橫,且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成為不可侵犯的一群。
其次是因工作安排存在著缺陷、內部資訊欠妥和體制不全等問題,主觀便駕於法律規定之上,濫用權力及專橫便成為遮掩不稱職的工具。
經驗告訴我們,查核公共行政工作人員是否在工作上受到“騷擾”的重要指標就是他們的健康狀況。受“騷擾”的受害者一般患有失眠、焦慮、抑鬱、厭食、全身疼痛、胃炎、消化系統不良等症狀,但若要去求診就醫,需在工作上補回求診就醫所花的時間。
最後,由於應價入或應監管者對導致發生此一令人惋惜的事情不加以重視,而以雞毛蒜皮和無關重要的小事,或以當作沒有發生過,一切如常的態度來看待,才令到應有改善的工作氛圍成為實現迫害、恐嚇和侮辱的好地方,而其受害者一般為低收入或前線的工作人員。
 公告
公告